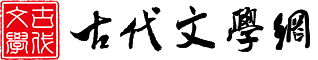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九月,监察御史张养浩上时政书万余言,列举朝廷十大弊端,“言皆切直,当国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构以罪罢之,戒台省无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元史·张养浩传》)。直到武宗死后,仁宗即位,他才再度被召,起用为右司都事。这首诗就是他回朝复官之后不久所作。诗中托物寄兴,以秋日梨花象征自己经历一番政治风雨吹打之后,再度焕发出异彩和芬芳。
梨花应是春季开放,而今秋季重开,本属病态现象。但诗人不是科学家,他只是托物寄兴,借物言情。所以,当他看到雪白飘香的花朵在萧瑟的秋风中再度开满梨树枝头时,于欣喜若狂之余,不禁诧异惊问:雪白飘香的梨花,早已被无情的春季信风从树枝上吹落干净、零落成尘了,是谁又派遣秋风(西风)使梨花再次还魂复活了呢?李白《宫中行乐词》有“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之句,故“雪香”即喻指梨花。开篇以惊叹怪问起笔,有耸人听闻之妙,又紧扣题面,为以下描写梨花姿容和抒发感叹作铺垫。
接着,诗人仔细观察这秋日梨花,写其与春日梨花的差异性和继承性:这秋日梨花在秋月清辉的照耀下,枝影疏朗,临风傲寒,更显冷艳挺秀;不像春天梨花那样浓密娇嫩,在明月下风移影动,花影婆娑,那般如梦似幻。然而它在微雨沾溉或露滴浸润时,依然不失“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娇容,仿佛带着春雨留下的痕迹,再度经受这秋雨的洗礼和考验。这两句通过对比,暗示出诗人经受了一场政治风雨之后,不像初入仕途时那样天真地耽于幻想,已经变得更加清醒、冷静,更加老成练达了;但那旧时风雨留下的痕迹并未泯灭,而应作为经验教训的积淀保留下来。“月影梦”“雨容痕”,既富有生动的形象意态,又蕴涵着深刻的反思理趣,正所谓“物物不物于物”,咏物而不为物所滞,方使物与我,物理与人情巧妙交融,浑然无迹。
第三联一笔宕开,在广义上抒发对秋色的新见:一般人只知秋风萧索,千林万卉,红衰翠减,因而总是“悲落叶于劲秋,喜桑条于芳春”(陆机《文献》)。于是由“草木无情,有时凋零”,进而益感人生易老,思急流勇退,发出了“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欧阳修《秋声赋》)的消沉感喟。自宋玉《九辩》悲秋以来,历代文人率多如此。而此诗却批判了这种“只知秋色千林老”的传统悲秋情绪,提出“争信阳和一脉存”的新见,实属难能可贵。是啊,人们的积习太深,怎么能相信这“秋色”原是与春天的阳光暖气一脉相承而存留下来的呢?
《周易》中八卦,七月乾上坤下是阴阳交泰,与正月坤上乾下,三阳开泰,其实阳气相当;八月巽上坤下是二阳四阴,比二月震上坤下,只少二阳。这是阴阳物理,故曰:秋季“阳和一脉存”。诗人以此象征人事,意在说明人在中年以后或中老年之间,不应壮志消沉,而应“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永葆青春活力,奋发有为才对。这是一种积极上进的人生观,却含蓄地寄托在咏叹秋日梨花的物理之中,尤觉警策而发人深省。诗人一反传统悲秋的陈套而自出机杼,并非纸上谈兵,试看他晚年六十高龄还变卖家产,赴陕西赈荒济民,终于心力交瘁而累死任所,则可见其老当益壮、“壮心不已”精神之可贵。
尾联再作转折,从人事说到“仙家”,但仍挽合到花开季节之事上。《续仙记》载:唐代道人殷七七于浙西鹤林寺使杜鹃花秋日开放;“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常于冬季令牡丹花开数色,每朵之上有一联诗,以预示其族叔韩愈的未来遭遇。诗人借用此典抒情,似乎也是在告诉人们:不要惊异殷七七与韩湘子太多事,让花在秋冬开放,因为仙家本来就不计较花开的季节是在寒季还是暖(暄)季。以“仙家”来对比世俗,曲折地表现了诗人不落流俗的眼界见识和胸襟抱负,且富有一种豪放潇洒和优游不竭的意趣。
此诗托物言情,通体比兴象征,立意新颖,不落窠臼。句句未离开秋日梨花的具体形象特征,却又无不暗合诗人的政治经历及人生感受,不即不离,不滞不脱。景物形象与人情理趣浑融无间。语言清淡朴素,言浅而意深,亦如秋日梨花那样素雅而芳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