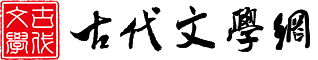横波亭在江苏赣榆县的河边,金时属青口辖区。金将移剌粘合驻防其地,“杨叔能,元裕之皆游其门,一时士望甚重。为将镇静,守边不扰,军民便之”(刘祁《归潜志》)。当时蒙古崛起北方并已南侵,破中都燕京,入潼关。曾经为宋人饱尝的民族耻辱,金人同样地尝到了;曾经为宋人抒发过的民族忧患与义愤,也出现在金邦的爱国志士笔下。青年元好问登上横波亭,感时的激情澎湃胸中,不能自已,因对青口统帅移剌粘合有所寄托,为他写下了这首气概不凡的七律。
笔立在河上的高亭,本给人以孤危之感;登楼远望,则会自然地引起一种古今茫茫百感交集的情怀。诗人首先就抓住这种深刻感受,写出豪迈的诗句:“孤亭突兀插飞流,气压元龙百尺楼。”注意“插飞流”这个说法,似乎本应写楼高插天,然而“突兀”二字已有横空出世之意,因而诗人还要多写一重险要,即横波亭的下临飞流,从而也暗点“横波”亭名之来由。第二句是对横波亭气势的比拟夸张。“百尺楼”本出自刘备对许汜说的一句盛气凌人的话,因为牵涉到陈元龙事(详前《论诗》析文),所以元好问熔铸为“元龙百尺楼”一语,辞采雄壮。大概是因其事本豪,而“元龙”这个字号也很大气的缘故,总之这一词语颇使诗人惬意,所以一再用到。但“元龙百尺楼”毕竟是子虚乌有的楼,所以说“气压元龙百尺楼”就格外有味。似乎天下临水之楼,竟无一可与横波亭比拟,只能拟之于想象中的“元龙百尺楼”。同时也暗用刘备语意,谓移剌粘合远非别的将帅可比。正是“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李商隐),期许之意贯彻篇终。
青口去大海很近,诗人面对“飞流”,很自然地想到这一点,同时在诗中将大海揽入,也更有气势。“万里风涛接瀛海”句出杜诗“万里风烟接素秋”(《秋兴》),而将时间范畴换为空间范畴。“接瀛海”点出江流去脉,而“万里”还兼关江流来龙,此句包括之大亦非杜莫比。紧接便是抚今怀古:“千年豪杰壮山丘。”无论是就时局还是登临题材本身而言,怀古似乎都是应有之义,这使读者联想到辛弃疾在京口北固亭写下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不同的是,辛词叹国中无人,而元好问诗庆金邦得士,那移剌粘合大将,是被包括在“千年豪杰”之内的。诗人这样推重其人,当然是有所期待的。
接下去似乎应该写写形势才对,然而诗人却用苍劲之笔画出一派江景,酷肖杜甫的《秋兴》:“疏星澹月鱼龙夜,老木清霜鸿雁秋。”句中平列六个名词和“秋”“夜”这一时间概念,疏星、澹月、老木、清霜形成一派清寒江景,雁唳长空,鱼潜水底,更增加画面的清寥。而在这一派苍凉惨淡肃杀的秋夜景色中,读者隐约可以感觉到时局艰危在诗人心中引起的忧患意识,它已不自觉地渗透在景物之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
《秋兴》有“鱼龙寂寞秋江冷”之句,为遗山诗所本。而此诗不言“寂寞”,“寂寞”与“冷”意转深。
诗的结尾进而化用《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抒发作者报国热情并以收复失地期许对方:“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其时金邦立足中原已久,作者以神州儿女自居是无可非议的,就像在南边唱着“何处望神州”的辛弃疾以神州儿女自居一样无可非议。爱国主义是中华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对汉人是如此,对女真人同样如此。令我们十分惊异的是,遗山此诗与辛弃疾在南方“过南剑双溪楼”写的《水龙吟》,从立意造境遣词用典上都十分神合。辛词就像是倒说过去的: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略为不同的是,辛词悲壮,元作豪壮。而强烈的爱国意识则并无二致。除了在行政地域上的敌对,可以说,两位作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已没有什么差异。由于政治上的对峙和时间上的接近,元好问似乎不大可能读到这首辛词。它们之间的神似,只能说是英雄同感,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