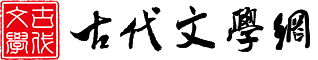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会分出高低,一般认为是品评孟郊的这首诗,实际上是一篇“韩孟优劣论”。孟郊字东野,中唐著名诗人,与韩愈齐名。他性格孤直,一生贫困,与贾岛一样以“苦吟”著名。韩愈形容他“刿目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贞曜先生墓志》);又给他的诗以相当高的评价:“有穷者孟郊,受才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不过,韩愈说孟郊可上继李杜,就不免有私阿之嫌。襟抱旷达的苏东坡是尊韩的,但不甚喜孟郊诗,以“郊寒岛瘦”并列而不赞成韩孟并称:“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要当斗僧(指贾岛)清,未足当韩豪。”但有时也表示欣赏:“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读孟郊诗二首》)而推崇苏轼的元好问对韩孟诗亦作如是观。
《六一诗话》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大体符合事实。此即首句“东野穷愁死不休”的最好注脚。《诗经·小雅·正月》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而孟郊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元好问就概括这些诗意来作为孟郊及其诗的形象性评语:“高天厚地一诗囚。”“诗囚”这个称号,恰当地概括了孟郊诗穷愁的主要特征及作者本人的主观看法,虽不如“诗仙”“诗圣”“诗豪”“诗鬼”那样被普遍地认可,要亦有充足理由。另一首《放言》中他干脆把贾岛也圈进来:“郊岛两诗囚。”“诗囚”这个称呼在这里显然是带有贬义的,在这一抑之后,诗人用韩愈作对比,对后者给以很高评价:“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韩愈曾被贬为潮州(即潮阳)刺史,故诗中以“潮阳笔”代指韩愈诗文,以“江山万古”予以标榜,则暗用杜诗“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意言其足以不朽。末句用《三国志·魏书·陈登传》的著名典故,陈登(字元龙)因不满于许汜碌碌无为,令其睡下床而自卧上床,许汜一直怀恨,刘备知道了却说,如换了他,则“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元好问把陈登事刘备语精要地铸为“元龙百尺楼”一语,说韩孟诗的比较岂止上下床之别而已。联系到韩愈“低头拜东野……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醉留东野》)等诗句,这里言下之意也有“退之正不必自谦”之意。
如果仅仅是扬韩抑孟,也只不过揭示出中唐诗中奇险一派两大诗人孰优孰劣的事实。但此诗的用心不限于此,它包含着更丰富的意味。元好问其实并不鄙薄孟郊,倒常常引孟郊自喻:“苦心亦有孟东野,真赏谁如高蜀州。”(《别周卿弟》)“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诗哭杏殇。”(《清明日改葬阿辛》)就作诗的苦心孤诣,情感真挚,不尚辞藻,不求声律而言,他与孟郊也有一致之处。然而正如苏东坡爱白居易,而又批评“白俗”一样。由于知深爱切,反戈一击,反容易命中要害。元好问对孟郊的批评,实际上也是爱而知其丑。赵翼《题遗山诗》有句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像元好问这样以国事为念的诗人,当然不会十分推崇孟郊那样言不出个人身世的作家。对于雄健奇创、有大家风度的韩愈,也就更为低首下心。在《论诗》中他曾两次通过对比表扬韩愈诗风,实有“高山仰止”的诚意。
元好问《论诗》系效法杜甫《戏为六绝句》而又有所发展。杜诗数首于作家只及四杰,而元诗常在一诗中比较两家,就是一种出新。此诗在写作上很注意形象性,因而说理议论中颇具情采,“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比“未足当韩豪”那种概念化抽象的诗句,也就更有韵味、更易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