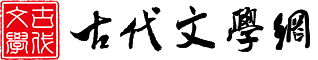当我们重读这一经典的时候,除了被那强烈的宇宙意识和由宇宙意识所升华的宇宙精神深深震撼之外,更被那作者诗意化的心理时空折服了。这种折服简直是哲学的征服,即诗化哲学的征服。
诗化哲学是德国浪漫美学。诞生于1795—1800年德国浪漫派哲学理论,在对工业文明的忧虑、反思和批判中,敏锐地发现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归宿与科学技术的尖锐冲突,于是“有限生命的永恒精神家园在哪里安放”就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诗学理论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诗美有重要的启示。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以江月起笔,可谓“横绝”。江连海,海生月,月照春江,这样一幅连环的美景呈现于千万里的阔大时空,极见诗人胸襟之大,眼界之广,有一种仰视宇宙的气魄。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之绕,花之林,汀之沙,用来衬托月之光。其美似霰,似霜,感觉的物化让人在静谧和清丽中获得瞬间的生命享受。心灵体验微妙极了。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皎月当空,江天无尘,一色净美。这美出自诗人的内心,又以何人何年来叩问:有限的个体生命能够超越时间的规定而获得永恒无限的价值吗?千古奇问,触入永恒之谜。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生命却一代传一代,没有穷尽,如同江月永恒于宇宙天地。莫非江月也属情种,它在等待自己的情人吗?如果江月有情的话,那么人就应该更有情;但是有情的个体生命有限,看看长江流水的永恒,那后浪推前浪不正像人类的代代相传吗?诗人似乎从宇宙天地顿悟到有限与无限的平衡。这是诗化了的时间,诗化了的哲学。施勒格尔说:“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说,永恒不是空无所有,不是时间的徒然否定,而是时间的全部的未分割的整体。在整体中,所有时间的因素并不是被撕得粉碎,而是被亲密地糅合起来,于是就有这么一种情况: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7世纪的中国诗人与17世纪的德国浪漫派诗哲达到了一种默然相契,这是多么有趣的中西对话!而且这样的对话是哲学的!
“白云一片去悠悠,清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永恒的时间里,情永恒,情纯洁;爱也永恒,爱也纯洁。“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由江天而游子,而思妇,由宇宙之大而人间相思,足见纯洁爱情是超时空的。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游子之思和思妇之词本来就是《古诗十九首》和古题乐府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在张若虚的笔下更加典型化和更加诗意化了。在浪漫美学那里,“所谓美不过就是客观化了的精神意义,美只能出自关照者的内心,它只能是有情感所激起的直观的内容。”由于审美直观排除的是经验的世俗的考虑,它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要返回内心以追求诗意化的心境,它要根据自我内心所体验过的内在时间重组重构一个新的时空心境,它要在把握的同一心境下把感性个体引出有限性的规定,达到“在主体的心意状态中所呈现出来的直观主体与直观对象的交融统一境界。”而且浪漫美学认为“真正的诗就是同一心境的客观显现。这是一个绝对超时间的永恒世界,人生价值的寄托之所。只有在那里,时间才被取消了,刹那凝化为永恒。”以此来观照在诗中出现的游子之思和思妇之词大概是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吧。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终以江月落笔,回扣起笔,同样妙绝。王尧衢《唐诗合解》卷三评曰:“此将春江花月夜一齐抹倒,而单结出个情字,可见月可落,春可尽,花可无,而情不可得而没也……千端万绪,总在此情字内,动摇无已,将全首诗情,一总归结其下。”斯言得之。不过,这里的“情”的确像是从浪漫美学所说的瞬间体验中得来。“个体在瞬间体验中,以想象为根基,不断把自己的过去投向未来,超时空、超生死,化瞬间为永恒。”从月出到月落,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无限时间;从碣石到潇湘,这又是一个地北天南的宇宙空间。诗人在想象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诗化时空世界,即“强烈的宇宙意识”和“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宇宙永恒,“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永恒,所以“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样,个体自我遂与永恒化一而成为宇宙之我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以江月起笔,以江月落笔,在仰观孤月、俯察江海的诗化巨大时空中使宇宙意识和人间真爱展示出美好的境界,在感悟人生有限和追寻人生归宿无限的心灵叩问中冥思永恒的千古之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评价委实不为过誉。
《春江花月夜》解读一,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自明代以后颇受评论家的重视和推崇,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称:“那是更迥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当我们重读这一经典的时候,除了被那强烈的宇宙意识和由宇宙意识所升华的宇宙精神深深震撼之外,更被那作者诗意化的心理时空折服了。这种折服简直是哲学的征服,即诗化哲学的征服。 诗化哲学是德国浪漫美学。诞生于1795—1800年德国浪漫派哲学理论,在对工业文明的忧虑、反思和批判中,敏锐地发现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归宿与科学技术的尖锐冲突,于是“有限生命的永恒精神家园在哪里安放”就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诗学理论对我们进一步理解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诗美有重要的启示。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以江月起笔,可谓“横绝”。江连海,海生月,月照春江,这样一幅连环的美景呈现于千万里的阔大时空,极见诗人胸襟之大,眼界之广,有一种仰视宇宙的气魄。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之绕,花之林,汀之沙,用来衬托月之光。其美似霰,似霜,感觉的物化让人在静谧和清丽中获得瞬间的生命享受。心灵体验微妙极了。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皎月当空,江天无尘,一色净美。这美出自诗人的内心,又以何人何年来叩问:有限的个体生命能够超越时间的规定而获得永恒无限的价值吗?千古奇问,触入永恒之谜。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类的生命却一代传一代,没有穷尽,如同江月永恒于宇宙天地。莫非江月也属情种,它在等待自己的情人吗?如果江月有情的话,那么人就应该更有情;但是有情的个体生命有限,看看长江流水的永恒,那后浪推前浪不正像人类的代代相传吗?诗人似乎从宇宙天地顿悟到有限与无限的平衡。这是诗化了的时间,诗化了的哲学。施勒格尔说:“从严格的哲学意义上说,永恒不是空无所有,不是时间的徒然否定,而是时间的全部的未分割的整体。在整体中,所有时间的因素并不是被撕得粉碎,而是被亲密地糅合起来,于是就有这么一种情况: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7世纪的中国诗人与17世纪的德国浪漫派诗哲达到了一种默然相契,这是多么有趣的中西对话!而且这样的对话是哲学的! “白云一片去悠悠,清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在永恒的时间里,情永恒,情纯洁;爱也永恒,爱也纯洁。“过去的爱,在一个永在的回溯所形成的永不消失的真实中重新开花,而现在的生命也就挟有未来希望和踵事增华的幼芽了。”由江天而游子,而思妇,由宇宙之大而人间相思,足见纯洁爱情是超时空的。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游子之思和思妇之词本来就是《古诗十九首》和古题乐府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在张若虚的笔下更加典型化和更加诗意化了。在浪漫美学那里,“所谓美不过就是客观化了的精神意义,美只能出自关照者的内心,它只能是有情感所激起的直观的内容。”由于审美直观排除的是经验的世俗的考虑,它对客观实在的认识要返回内心以追求诗意化的心境,它要根据自我内心所体验过的内在时间重组重构一个新的时空心境,它要在把握的同一心境下把感性个体引出有限性的规定,达到“在主体的心意状态中所呈现出来的直观主体与直观对象的交融统一境界。”而且浪漫美学认为“真正的诗就是同一心境的客观显现。这是一个绝对超时间的永恒世界,人生价值的寄托之所。只有在那里,时间才被取消了,刹那凝化为永恒。”以此来观照在诗中出现的游子之思和思妇之词大概是不会有理解上的障碍吧。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终以江月落笔,回扣起笔,同样妙绝。王尧衢《唐诗合解》卷三评曰:“此将春江花月夜一齐抹倒,而单结出个情字,可见月可落,春可尽,花可无,而情不可得而没也……千端万绪,总在此情字内,动摇无已,将全首诗情,一总归结其下。”斯言得之。不过,这里的“情”的确像是从浪漫美学所说的瞬间体验中得来。“个体在瞬间体验中,以想象为根基,不断把自己的过去投向未来,超时空、超生死,化瞬间为永恒。”从月出到月落,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无限时间;从碣石到潇湘,这又是一个地北天南的宇宙空间。诗人在想象中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诗化时空世界,即“强烈的宇宙意识”和“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宇宙永恒,“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永恒,所以“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这样,个体自我遂与永恒化一而成为宇宙之我了。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就是这样,以江月起笔,以江月落笔,在仰观孤月、俯察江海的诗化巨大时空中使宇宙意识和人间真爱展示出美好的境界,在感悟人生有限和追寻人生归宿无限的心灵叩问中冥思永恒的千古之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评价委实不为过誉。
https://www.gudaiwenxue.com/shangxi/13.html